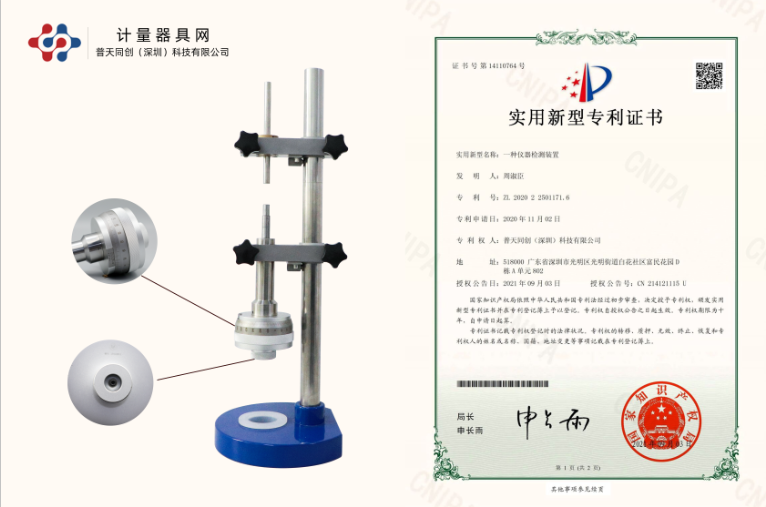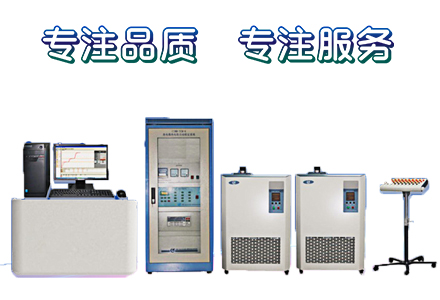就像游戲《大富翁》,每個從天而降的角色來到土地上只有一個買地蓋房、蓋大房的夢想。
小時候看《了不起的蓋茨比》時,非常向往里面每周舉行的宴會—“在他蔚藍色的花園里,男男女女像飛蛾一樣在笑語、香檳和繁星中間來來往往……客人從他的木筏的跳臺上跳水,或者躺在他的私人海灘的熱沙上曬太陽……”不是向往香檳、私人海灘,而是向往蓋茨比每周的豪華宴會背后的故事—他從少年時就深愛著一個姑娘,那姑娘嫁了有錢男人,從窮小子變成富翁的他在有錢男人的別墅附近買下一幢別墅,每周的宴會僅僅為了那姑娘能夠被熱鬧吸引過來,給他個順訪!
這故事使我對有錢人充滿好奇,特別是白手起家的這種—我以為他們奮斗的動力都是浪漫史,也以為不管他們一路跋涉得多么艱辛,都會固執、溫柔地呵護最初的夢想。

L顯然是個有錢人,但是他自己還不太確定,否則,就不會邀請我們去他的別墅做客,幫忙給他的財富和品味做個鑒定。
我們抵達他的別墅時,已是深夜。他很自豪地將車隨便停在車道邊:“環山的這整條車道都是我私人的。”很深的墻,很大的紅門,他卻打開旁邊一扇小門供我們魚貫而入,“大門太重了,難開難鎖。”門后的世界大得超出我們想象,黑夜和花園魚池混在一起,一只大狗憤怒焦急地在鐵柵欄后咆哮。“保姆剛辭掉,還沒有換新的,所以有些冷清。”L帶我們參觀。別墅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三個地方:巨大的佛堂—三層樓里只有這間佛堂香燈常明,略有人氣;巨大的書架—空蕩蕩,唯有第一層稀疏地擺了一排盜版的金庸武俠小說;巨大的浴室—八十平方米的浴室里最多的是灰塵,L很少使用這多功能超大浴缸,他每天都是在外面足浴后再回家,他也同意這樣的浴室展覽價值大過實用價值。
我不想評估好品味或者壞品味,只想在別墅里尋覓到蓋茨比那種溫柔的夢想。但是,沒有女人的痕跡,也沒有小孩。四十多歲的富豪L很自豪地說:“我不會帶女人回來。”L不提老婆,但是不介意說孩子:“孩子不用來這兒,他太小,房間太多,而且上學不方便。”至于父母—“他們住慣了自己的房子,這里沒有朋友,出門也不方便。”回答我們這些八卦盤問時,他正安撫著那只寂寞得有些躁狂的狗,狗和他在燈光下被拉出一條又長又冷清的影子。送我們離開時,L用手匆匆指了指遠處的空地:“那一畝地也是我的,我打算再蓋一幢別墅。”
這個季節的風已經很冷了。我打著哆嗦沖進車里。空調開得很暖和,但是當我想到一個人一條狗一個保姆住在占地幾畝的別墅里時,又哆嗦了起來。
L和我們告別時,有些遲疑,一再地問我們要不要去吃點夜宵。我們用哈欠表示睡意很濃,他沮喪地下了車。他的身影很快變成了一個小黑點被甩在車的后方,同行的人說:“我要是他,我會不敢回家的。”“他還要再蓋呢。”另一個人說。“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,蓋了做投資放在這兒,自己到城里和孩子、爸媽一起住不是挺好。”
也許,L先生最初的夢想就是有很大的房子?就像游戲《大富翁》,每個從天而降的角色來到土地上只有一個買地蓋房、蓋大房的夢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