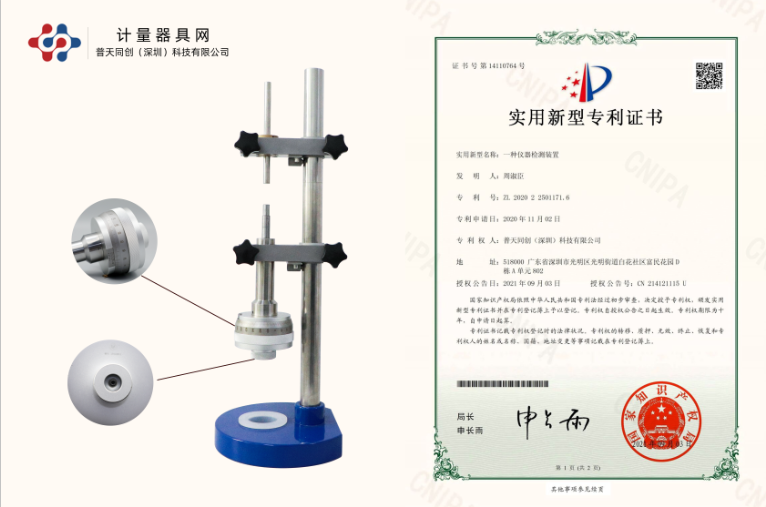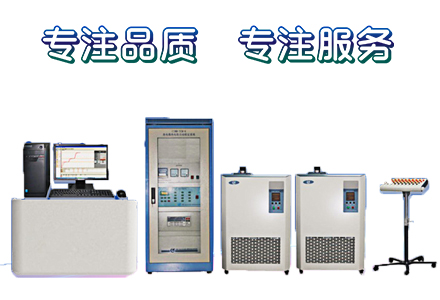這些天我抱病了,在夕陽下我不能外出,就像嫩芽不能注視外面,就像車禍發生時的人沒來得及探出頭來,就像逶迤的小路盡頭都是懸崖。
醒來前我想好了去哪。有時,一些想法如同一根魚刺,那一大片的塋地,天主教的小鎮,帶著祭品涌入人群中撒野。就在那里,快向那奔跑,就在那里,回望幸福的末日。額頭上的眼睛為了加冕,夜歸的掌燈人直到四壁坍塌。干涸的眼淚在太陽下,與無法結束的一生。
月光下的墨池旁哭泣的人,仿佛,失去了以什么為中心。夢到了遙遠的二十世紀……今晚,螢火蟲肆虐堂廳,一切像貴夫人緩緩地走下樓梯,想起往年在朝廷上的篝火舞曲。老夫愛著擅長的魚鱗書法,老夫效仿著酒鬼和孤獨,硯臺成了無以抗拒的家。
一只鳥,一塊冰或者是一棵栗子樹,在荒蕪中植下心靈,變得厚顏無恥。一潑豪墨,依然變得厚顏無恥。一座嫣然南山,史無前例地厚顏無恥。你在囈語,為什么我每天重復生活,卻無法朝著白云的方向成長。